马上注册登录,享用更多感控资源,助你轻松入门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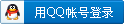 |
|
×
相比脚踏实地的小说,诗歌就是天马行空了,到处是诗的痕迹。
梁宗岱(1903-1983年)译的莎士比亚(1564-1616年)十四行诗,力图押韵:
对天生的尤物我们要求蕃盛,以便美的玫瑰永远不会枯死;
但开透的花朵既要及时雕零,就应该把记忆交给娇嫩的后嗣。
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,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。
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的句子:
上帝爱一片懒散的虹,不亚于工作的海。
年轻时,自己特懒散,于是将上面的诗句引为知己。
中国的现代诗人戴望舒(1905-1950年)描述年轻人自以为渐入老境:
老实说,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了:
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,
而对于春月秋花却又太老。
他的小诗《我思想》也不错:
我思想,故我是蝴蝶……
万年后小花的轻呼,
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,
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。
金克木(1912-2000年)以学问家著称,但他的《邻女》中的一段也写得颇有意味:
你换上一件绯红的春装,
我的窗上便映出一片霞光。
你再换一件深黑的素服,
我的窗上又有了迷的烟雨。
你的四季在身上变换,
我的四季却藏在心里。
美国诗人与散文家《爱默森文选》中的不朽语句:
如果我的小船沉没,它是到了另一个海上。
废名(冯文炳)(1901-1967年)的《雪的原野》:
雪的原野,
你是未生的婴儿,
明月不相识,
明日的朝阳不相认——
今夜的足迹是野兽么?
树影不相识。
雪的原野,
你是未生的婴儿——
灵魂是那里的人家的灯么?
灯火不相识。
美国女诗人狄更生(l830-1886年)的《虫鸣》:
日午时最感到古意悠扬,
当八月焚成了残烬,
遂唤起这幽灵似的音乐,
作为安思的象征。
迄今盛行犹未见减色,
光彩也未显皱纹,
但是一种神奇的变化,
已侵入自然本身。
她的另一首《冬日的下午》的“通感”妙极了:
冬日的下午往往有一种
斜落下来的幽光,
压迫着我们,那重量如同
大教堂中的琴响。
奥地利诗人里尔克(1875-1926年)的抒情诗《童年纪事》(“盯住她被戒指扭曲了的手指,看见它们在白键上移动,仿佛艰难地走在雪野里。”和《秋日》:
谁此刻没有屋,就不会再造屋,
谁此刻孤独,就会长久孤独。
英国诗人格雷(1812-1898年)的《墓畔哀歌》:
他给予坎坷一切他所有的,一滴眼泪,
他得自上苍一切他所求的,一个朋友。
爱尔兰诗人叶芝(1865-1939年)的《偷走的孩子》也哀伤:
走吧,人间的孩子!
与一个精灵手拉手,
走向荒野和河流,
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,你不懂。
他的《第二次来临》中的一个段落:
显然某种启示就要来临,
显然第二次来临已经很近;
第二次来临!这几次还在口上,
出自世界之灵的一个巨大形象,
扰乱了我的视线:沙漠中的某个地点,
一具形体,狮子的身,人的面,
像太阳光一般,它那无情的凝视
正慢慢地挪动它的腿,到处是
沙漠中鸟儿的影子,翅膀怒拍,
黑暗又降临了,但我现在已明白,
二十世纪的死气沉沉的睡眠
给晃动的摇篮摇入恼人的梦魇。
什么样的野兽,终于等到它的时辰,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,来投生?
伯利恒是耶稣降生的地方,诗中的寓意不言而喻。
希腊诗人埃利蒂斯(1911年-)的诗篇有着肃穆、庄严和伟大感:“又要爱又要梦想,那是犯重婚罪。”“我的上帝,你费了多少蓝颜料来防止我们看到你!”“在我的语言之乡,忧愁就叫发光体。”“人类倾向上帝,就像鲨鱼为血所吸引一样。”“一个构成错误的海是不可能存在的。”
又如:
就是那么久的时间,
如拍岸的浪花要磨光一颗卵石,
或者黎明时天空的清冷要显现,
一株紫色无花果的外观。
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(1893-1930年)的《穿裤子的云》,按现在的流行语,是“太强了”,最后一段:
当
以骚乱宣布着
它的到来,
你们向救世主奔去时——
我给你们
掏出灵魂,
踏扁它
使它变得更大!——
把这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你们,作为旗帜。
法国现代诗人艾吕雅(1895-1952年)的《溺水者》:
石头在水面蹦跳,
轻烟不能透入水中。
水像谁也不能伤害的
一块皮肤
却接受人和鱼的
爱抚
被人捉住的鱼挣扎击水,
发出弓弦般的鸣响,
它要死了,再不能
吞咽这世界上的空气和阳光。
而人也沉入水底
为了鱼
或者为了柔软但始终严闭的水面
那难熬的孤独
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(1892-1923年)的《紫色的曙光》:
我随身携带紫色的曙光来自我的远古时代,
赤裸的处女们和奔驰着的山陀嬉戏……
金灿灿的日子目光明亮,
只有阳光向一位温柔的女人的躯体致意……
男人没有到来,他不曾存在,永远不会存在……
男人是一面被太阳的女儿愤怒地掷向峭壁的虚假的镜子,
男人是一种谎言,白色的孩子们不懂的谎言,
男人是一颗被骄傲的嘴唇的拒绝的腐烂之果。
漂亮的姐妹们,攀登那最坚硬的岩石,
我们都是女战士,女英雄,女骑手,
是贞洁的眼睛,天空的眉毛,玫瑰色的幼虫,
是沉重的激浪和惊走的群鸟,
我们是最意外的期待和最深的红色,
是老虎的斑纹,绷紧的弓弦,不怕眩晕的星星。
女诗人把男人损得多厉害啊。
美国诗人沃莱斯·斯蒂文斯(1879-1955年)的《面包干》中叙述的人类和自然界的盲目性:
鸟儿仍旧飞来,一群群犹如流水,
只因为这是春天,鸟儿必须飞来。
当然,士兵也必须行进,战鼓也必须轰鸣、轰鸣、轰鸣。
——悲剧的时代!悲剧的国度!
生活其中,悲剧总是相同。 |